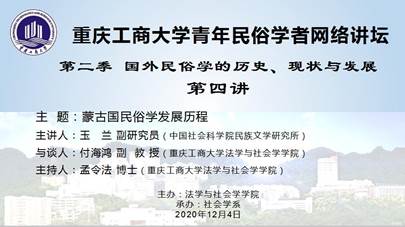
2020年12月4日晚,由重庆工商大学环球360游戏网站主办,环球360游戏网站社会学系承办的“重庆工商大学青年民俗学者网络讲坛(第二季)”第四讲——“蒙古国民俗学发展历程”在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此次讲坛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玉兰博士主讲,我校环球360游戏网站民俗学教师付海鸿副教授与谈、孟令法博士主持,校内外百余名名师生共同参与。
蒙古国是我国重要的陆上邻国,其民俗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大影响。近百年来,蒙古国民俗学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民俗学资料及和文著,不仅展示了蒙古国的物质民俗、精神文化形式,还清晰呈现出蒙古国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传统特征和当代形态。基于对蒙古国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分门别类的研究,玉兰老师从梳理蒙古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并详细讲解了蒙古国民俗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蒙古象征学。
一、蒙古国民俗学发展历程

玉兰老师介绍,将“民俗学”三个字一一对应到蒙古语中,可译出“arad-un bilig jui”这个词。然而,蒙古国却很少使用这个术语,因为在当地,民俗学很少作为一门学科或专业出现,而更多地以口头文学或民间文学(aman johial)的形式出现,这种定位深受前苏联学科传统的影响。蒙古国民俗学研究的阵地主要有两个:蒙古国科学院语言与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而这两者皆建立于1931年成立并于后来更名为蒙古国科学院的蒙古国经书院。
接下来,玉兰老师对比了蒙古国民俗学研究和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几个阶段,认为两者大致相同。以1921年蒙古国经书院的成立为起点,她将蒙古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1-1950年代,该阶段民俗学研究的工作主要是搜集、记录、分类,建立资料库。这期间不仅建立了语言文学研究所,还发布了“记录民间口头文学的基本准则”,而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宾·任钦,精通多国语言,包括俄语、德语、匈牙利语等,曾在德国威斯巴登上发表了《蒙古民俗》。这套书为德国、蒙古国乃至欧洲的民间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也为蒙古国后世的民俗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蒙古国对蒙古民族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相对较早的,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民间文学资料;同时,蒙古国早期的民间文化研究者的搜集和记录方法也是较为科学的,他们通常以语音音标记录或转写,这使他们的研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第二阶段是1950-19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将搜集的资料进行分类和体系化,形成科学文本。如普·浩日劳、嘎·任钦桑布、舍·嘎丹巴以及乌·扎格达苏伦等学者就对蒙古国民间文学资料做了系统梳理,给出了一系列定义与举例说明。
第三阶段是1980-2000年,该阶段的研究者主要进行的是学术研究,以及民间文学概论及各文类的研究等。此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哈·桑皮勒敦徳布,就出版了大量专著、资料集及论文,还合作编辑出版了99卷《蒙古民间口头文学大系》,这对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起到了深远影响。而S·巴达玛哈丹编著的《蒙古国民族学》,则展示了蒙古各部落的饮食、文化、服饰以及风俗等状况,并从考古学角度对蒙古国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介绍,从而呈现了蒙古各部族文化从早期差异极大到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
第四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目前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主要有普·浩日劳的《蒙古民间文学中的审美思想》和S·杜拉姆的《蒙古象征学》等。
玉兰老师指出,国内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阶段跟蒙古的大致相同,大概是因为国内蒙古学领域的多数学者都曾通过国家留学委基金项目赴蒙古国留学,近些年两国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根据满都呼老师的研究,两国划分的研究阶段主要不同在于,国内蒙古族民间文学有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罗布桑却丹于1918年出版的《蒙古风俗鉴》。这部书是蒙古族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志。后世的一些民俗志只取了其骨架,只见习不见人,而《蒙古风俗鉴》则不仅可以见习见人,而且见人的心理和性格,并贯穿了两个视角,一是比较的视角,一是批评的视角。此外,两国的民间文学分类也不同。国内民间文学分为散文体口头文学和韵文体口头文学,而蒙古国民间文学却是以有无曲调为标准来分类的,即分为有曲调的民间文学和无曲调的民间文学。
二、蒙古象征学

象征学的蒙古语是“belgedel jui”,但这个词“没有办法精确定义”,因为它似乎可以代表许多术语的意思。蒙古语中,“象征”(belge-del)一词的词根是“吉祥”(belge)。蒙古谚语“吉祥的语言造就永恒的吉祥”,就包含了蒙古人对美好的向往,很难用西方术语来概括。玉兰老师讲到,在蒙古民间文学中,几乎所有情节、数字、方向、颜色、形状以及动物等都具有象征意义,且这些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语义学意义,可以说语义学意义已经非常模糊。
玉兰老师举例说,在蒙古神话中,有很多数字,如“99个天”等。国外蒙古学家一开始就在统计这个“99重天”都包含哪些“天”。还有蟒古思故事普遍认为有“18部”,每一部都要消灭一种蟒古思,但18部到底都是哪些蟒古思,目前尚未定论。研究者们疑惑这些语词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于是运用个案研究法,发现有的关联是因为神话传说形成的,有的则是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有关。S.杜拉姆先生并不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是依据早期蒙古神话研究、海量民间文学文本的分析与田野调研,对“蒙古象征体系”做了系统研究。
玉兰老师举了两个关于象征体系的例子:
一是方向的象征。方向的象征依据的是蒙古创世神话,神话中就有方向与五个元素、五个颜色、十二属相等内容的结合。方向的象征体系中有一个中心,外围八个方位。中心代表黄色、土、蒙古;东代表青色、木、兔;西代表白色、铁、鸡;南代表红色、火、马;北代表黑色、水、鼠。东半边(特别是东北方的“牛/虎”)是比较凶险的方位,需要男性“镇压”,所以是男性区,放置马鞍、马奶桶等男性用具;西半边是女性区,放置锅碗瓢盆及橱柜等女性用品。方向的象征意义在很多时候都是固定的,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都会有体现。

二是数字的象征。蒙古民间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数字有3及3的倍数,4,5,7及7的倍数,以及9。3代表的是稳定、全面或高尚的意思,比如蒙古民间文学文类中有三三句,将宇宙中所有的现象都以“三”的形式来总结。4的出现往往表明四个方向或一年四季。5常常用在颜色和元素中。此外,如果出现颜色的话,要么是黑白对立,要么是用五色形容。这个数字也是比较完美的数字,因为它是最小奇数和最小偶数的和。7和7的倍数则总用来表明经历困难的次数,比如英雄打败敌人往往需要七天七夜等。9的话,显然是3的3倍,又是最大的个位数,所以它是蒙古民间文学和生活习俗中最为高尚的数字。
数字的象征体系则是一个中心,围绕四个方向。中心是2+3=5,东是6、8、12,西是2、4,北是13、33、9、99,南是7、77等。偶数放在东西两侧主要是起一个平衡的作用,而北边的数字与天界相关,南边的数字则与冥界相关。中心点是奇数和偶数的交叉点,代表人间。跟天界相关的这些数字非常常见,比如敖包的数量总是13个,要么是左右各六个,加上中心一个;要么是前后左右都是三个,中心一个。因为敖包是人和天界沟通的重要场合,所以它的数量和位置都是有规定的。
玉兰老师认为,虽然各国都有研究者认为蒙古史诗没有历史性和英雄性,甚至还有“过于夸张、文学审美价值极低”的评价,但无法否认的是,对于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地理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气候寒冷地方,并且战争不断的蒙古人民来说,史诗带有强烈的抚慰作用。也就是说,人们需要这种民间文学的语言和象征意义作为抗争手段。总而言之,蒙古象征学的探讨,对于正确理解蒙古民间文学和蒙古民俗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总结与讨论

在互动交流环节,孟令法博士首先对玉兰副研究员的详细讲解表达了衷心感谢,然后表示国内的民俗学研究同样会关注颜色、数字、方向等的象征意义,但这些象征没能形成体系。孟令法博士认为,这场讲座使我们更加了解了邻国,而与领国的学术交流还对国内的民俗学研究有推动作用。与谈人付海鸿副教授认为,这场讲座具有一个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认知视角,让我们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游走于其他东亚国家。另外,付老师认为,蒙古国和中国的民俗学发展有交叉,而且中国的早期民俗学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付老师还问到,蒙古国的民俗学学科设置情况如何?想从两国学科设置的对比中收获更多信息。玉兰副研究员解答到,蒙古国的民俗学比较晚才开始院系的设立,最开始只有民间文学研究,研究地也只是蒙古经书院的研究室,直到1961年左右才独立成蒙古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听众反馈非常热烈。如有听众问到,国内是否有S.杜拉姆《蒙古象征学》一书的中译本,玉兰老师则表示目前还没有,对此她将继续跟进。另有听众问到,蒙古国的民俗受到佛教影响了吗?玉兰老师表示,蒙古民俗是受佛教影响很深。自从成吉思汗时期接受藏传佛教后,蒙古地区基本是全民信仰佛教,现在都很难说清该地区哪些民俗是蒙古族本有的,哪些是佛教带来的,佛教渗入到蒙古民俗学的方方面面。还有听众问到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蒙古族史诗《格斯尔》的区别,玉兰老师回答到,两部史诗虽在故事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蒙藏两族的交流关系,然而二者的区别却是显著的。对这一问题,回答起来的确有些复杂,不过可以简单举两个方向来说明,即不仅可从史诗内容中的女性英雄之“善恶”属性的对立层面加以探查,还可从男性英雄的死亡和复生角度予以理解。就前者而言,《格萨尔》中的女性英雄是善恶对立的,而《格斯尔》中的女性则多是善恶融合;就后者而言,《格萨尔》中的男性英雄基本都是死而不复生的,但《格斯尔》中的男性英雄在前一部的结尾升天,却在下一部中又复生参加战斗。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蒙古民族对生活环境和征战历史的社会记忆是与藏民族是不同。还有听众问到,蒙古族史诗十分多样,现已整理出版的又有多少?对此,玉兰老师回答到,目前发现的蒙古族史诗大致有500部,且基本完成出版,但文字则以蒙古文为主。
通过这次讲座,玉兰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蒙古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和蒙古象征学,让我们了解到蒙古国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发展状况,启发了两国比较研究的可能路径。在此,再次感谢玉兰老师的精彩讲述,感谢参与本次讲座的校内外老师和同学们的大力支持。



